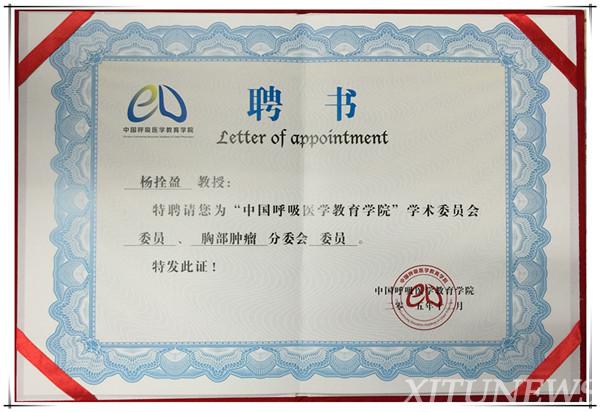
本文目录导航:
中国呼吸医学有哪些新进展?
呼吸疾病是包括轻如自限性的普通感冒、重如威胁生命的细菌性肺炎或肺栓塞等一系列发生于呼吸系统的疾病。
美国每年有1亿的感冒患者,英国七分之一的人罹患慢性气道疾病,主要是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和支气管哮喘。
在加拿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占住院病人的10,16的患者因呼吸疾病而死亡。
在中国,呼吸系统疾病高居死亡原因第三位,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呼吸疾病,500万人因此丧失劳动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呼吸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呼吸医学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文将回顾过去几年里中国专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包括COPD、哮喘、肺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肺部感染、肺栓塞及阻塞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等主要呼吸病种在发病机制、预后及治疗方面的新进展。
慢性阻塞性肺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至2020年COPD将位居我国疾病经济负担的第一位,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五位。
一项大样本的、以肺功能为基准的有关COPD患病率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年人、吸烟者、低体重指数、受教育程度较低、厨房通风不良、职业接触粉尘或生物燃料、儿童时期罹患肺部疾病和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中COPD的发病率显著增高。
室内污染物尤其日常使用生物燃料可能是中国南方农村人群罹患COPD的另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现今已阐明COPD的部分遗传易感性。
亚洲人群COPD 的部分遗传易感性与EPHX1 113和EPHX1 139基因多态性相关,而COPD总的遗传易感性则与EPHX1的表型具有相关性。
TNF-α和ErbB3也参与了COPD的发病过程, 同时二者还介导了TACE在COPD病程的作用。
一项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对照的研究结果显示:吸粘液溶解药羧甲司坦是防止中国COPD患者急性加重的有效药物。
并且,羧甲司坦的预防作用与COPD的严重程度、吸烟和吸入皮质激素均没有相关性。
另一项研究显示小剂量的缓释茶碱尽管不能改善肺功能,但对于稳定期COPD的患者仍能改善症状且有很好的耐受性。
沙美特罗/丙酸氟替卡松(舒利迭,葛兰素史克公司产品,英国)的治疗能够持续改善COPD患者的肺功能、生活质量和症状,且在中国人群中耐受良好;并且,对于既往存在吸烟史的患者,肺功能的改善更为显著。
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哮喘是众多细胞及细胞因子参与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嗜酸粒细胞特征性存在于支气管哮喘患者气道管腔内,并在体内促进MHC II类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进而激活T 淋巴细胞 。
管腔内嗜酸粒细胞向引流的气管旁淋巴结移行,聚集于富集T 细胞的皮质旁区,进而刺激体内抗原特异性的 T 淋巴细胞增殖。
此外,嗜酸粒细胞还可在体内通过增强Th2细胞反应来调节免疫反应 。
CD34+ 干细胞的迁移和原位分化促进了炎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在支气管哮喘小鼠模型中应用抗趋化因子受体3的抗体可以抑制CD34+ 干细胞的迁移和分化 。
哮喘大鼠经抗原激发后表达高水平的白介素 (IL)-4和Th2类细胞因子。
气道上皮细胞通过释放全身炎症介质启动炎症反应,并且通过免疫病理反馈调节过敏性鼻炎和哮喘。
对哮喘患者的临床研究显示: B7-1/B7 2-CD28/CTLA-4 分子均不同程度地在各种细胞表面表达,并以溶解分子形式存在于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内,这对于维持Th1/Th2的平衡非常重要 。
过敏症患者体内CD4+CD25+ T细胞的抑制功能下降。
CD4+CD25+ T 细胞通过下调Th2活化所需要的细胞因子,从而抑制Th2反应。
刘等进行了汉族120 例哮喘患者与116例健康对照者中关于ADA基因三个多态性位点:ADA1、ADA2和 ADA6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与哮喘易感性有关的DNA 序列定位于ADA1和ADA2 位点之间。
这可能成为支气管哮喘治疗的新策略。
动物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接种卡介苗能更好的调控Th1/Th2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减轻变态反应性气道炎症。
进一步研究气道过敏性疾病靶向治疗的作用,有助于建立有效的联合治疗哮喘的方案。
一项对527位门诊病人的问卷调查研究显示,随着近年来对哮喘长期管理工作的重视以及哮喘规范化治疗的推广,哮喘总体控制水平有明显改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
SARS是最近出现的一种可以大范围流行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病原体是一种新型的冠形病毒菌株,很可能起源于野生动物。
病房环境和管理对预防院内爆发SARS非常重要。
这次SARS爆发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和经验来预防SRAS的再发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的袭击。
SARS的发病机制复杂,最为合理的解释为SARS-CoV对靶细胞的直接损伤以及继发的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导致的间接损伤。
IL-6, IL-8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的迅速升高是二次感染的信号,死亡率极高。
SARS-CoV可以侵及中枢神经系统, 单核细胞因子参与SARS脑部免疫病理的过程 。
用ELISA检测SARS-CoV N199蛋白的方法可以用于临床诊断和SARS-CoV感染的筛选。
Lu等人用质谱决策树分类算法来进行SARS的初步鉴定,有望成为早期诊断的有效工具。
SARS患者可以在2年内免受SARS-CoV的再感染 。
动物研究提示短干扰RNA的研发作为冠状病毒靶向治疗的药物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
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SARS病人使用激素治疗并不能降低个体死亡率与住院天数,但能够降低整体死亡率和即刻死亡率并且缩短整体的住院时间。
胸膜疾病
水通道蛋白-1可能参与了病理状态下胸腔液体的转运。
大鼠胸膜间皮细胞上表达水通道蛋白-1。
结核性胸腔积液(TPE)中水通道蛋白1的表达增加,并认为可能与TPE 的形成相关。
针对水通道蛋白1的shRNA能显著抑制大鼠胸膜间皮细胞上水通道蛋白1的表达。
RNA 干扰有望成为体内研究胸腔积液机制的有效工具。
淋巴细胞性胸腔积液是指胸腔积液中淋巴细胞的数量占白细胞总数的50以上,恶性肿瘤和结核性胸膜炎是其主要的病因,约占90以上 。
CD4+CD25+ 调节T细胞数目在恶性胸腔积液 (MPE) 和结核性胸腔积液(TPE)中均显著增加,并通过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抑制CD4+CD25C T细胞的增殖 。
CD4+CD25+ 调节T细胞募集入胸膜腔的机制与胸膜细胞局部产生的IL -16 或趋化因子CCL22的作用相关。
临床上鉴别TPE 和MPE非常重要。
很多研究表明IFN-γ的测定对胸腔积液的诊断有很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虽然腺苷脱氨酶对于结核性胸膜炎的诊断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它的总体准确度要比IFN-γ低。
癌胚抗原是应用最广泛的肿瘤标记物,它是确诊恶性胸腔积液非常有用的诊断工具,还常被用于恶性胸膜间皮瘤和转移性肺癌的鉴别。
现有的证据不推荐单独应用CA-125, CA 15-3, CA 19-9和CYFRA 21-1来诊断恶性胸腔积液,但meta分析显示联合检测多种肿瘤标记物的敏感性更强。
对胸膜髓系细胞-1上的可溶性触发受体的检测可以帮助医生区分胸腔积液是细菌性的还是其它原因造成的。
肺部感染
免疫抑制患者的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徐等已证明:免疫抑制大鼠的肺炎模型中,角质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低于正常免疫能力的大鼠 。
侵袭性肺曲霉病是一种常见的坏死性肺炎。
最近的研究表明,树突状细胞可以吞噬曲霉分生孢子。
IL-12基因转染的树突状细胞可以显著增强曲霉特异性的IFN-γ反应,从而提高曲霉菌肺炎患者的存活率 。
提示抗原刺激的树突状细胞和IL-12基因疗法可以作为曲霉病的辅助治疗。
Zhan等人描述了患有慢性呼吸系疾病(CRD)的危重病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的临床特征并且评估了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价值。
随着肺部浸润病灶的迅速扩展,出现支气管伪膜、外周血白细胞的迅速增高以及影像学的恶化。
在浸润之前早期给予抗真菌治疗的患者均存活下来。
慢性呼吸系疾病(CRD)的危重病人中罹患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并不少见,并且预后较差。
根据临床特点进行早期诊断和经验性治疗有望改善患者的预后。
最近,He等人在原子水平上详细阐述了禽类的AIV病毒从N-端的PB1到C-端的PA的结构。
一个对120个中国志愿者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用小剂量灭活的AIV疫苗加上水合氢氧化铝佐剂所引发的免疫反应和由佐剂或者无佐剂分裂病毒疫苗引发的免疫反应基本等效。
临床研究表明被动免疫疗法是治疗AIV感染的一种可行方案。
粘液高分泌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大进展。
粘液高分泌是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和囊性纤维化等慢性炎症疾病的特点。
伴随着杯状细胞增生和 MUC基因异常,粘液高分泌会导致粘液纤毛清除率减退,非正常菌群定植,气道粘液栓形成以及气体交换的障碍。
Gob-5和AQP5强大的渗透性水通道是调节哮喘粘液高分泌的重要基因。
慢性气道炎症中,气道上皮细胞在整个炎症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IL-13, IL-4和IL-9都是在气道炎症过程中引起粘液高分泌的重要细胞因子,TNF-α也可以通过PKC信号转导导致粘液高分泌。
此外,上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也可以引起粘液高分泌和上皮细胞的增殖。
研究指出富含丙氨酸的豆蔻酰化的激酶C底物(MARCKS)是中心调控分子。
总之,现已逐渐阐明粘液分泌及粘蛋白表达的调节机制。
肺癌
关于基于顺铂和卡铂的化疗方案治疗进展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是否等效的问题已基本有了答案。
Meta分析显示,顺铂和卡铂的化疗方案组均没有明显的生存优势。
最近一项meta分析显示胸腔冲洗液细胞学的检查对肺癌患者的生存及预后有很大的帮助。
陈等研究了97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发现组织因子(TF)促进血管生成,而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受体(uPAR)则促进淋巴结和血行转移。
TF和uPAR的共表达在NSCLC的转移和预后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一些罕见的肿瘤,如原发性肺滑膜肉瘤的不诊断依赖于显微镜辨别上皮样或梭形细胞,或免疫组化证实细胞角蛋白、波形蛋白和上皮膜抗原染色阳性。
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最近,人们研究ARDS的治疗时发现,姜黄素通过抑制NF-κB介导的炎症基因的表达来保护机体免受肺移植相关急性肺损伤。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血管形成素-1(Ang-1)对脂多糖型急性肺损伤的治疗有协同作用。
Ang-1基因修饰的骨髓间质干细胞可望成为治疗急性肺损伤的新策略。
Sun等人研究认为姜黄素(CUR)通过改善氧化应激和抑制NF-κB介导的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来减轻急性肺损伤。
因此,姜黄素可能成为治疗缺血再灌注肺损伤的新方法。
Jin等人指出ARDS患者血清的IL-6水平的升高与肺损伤的严重程度相关,并能与APACHEII 评分联合判断疾病的预后。
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RRT)可以降低血清中IL-6的水平,减少机械通气和ICU的入住时间,降低呼吸机相关肺炎(VAP)的发生率。
CRRT可能是治疗ARDS最重要的方法。
肺栓塞
内皮细胞溶解纤维蛋白的功能在肺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学中起了重要作用。
尿激酶型纤维蛋白酶原激活剂与其受体的结合可能是尿激酶型纤维蛋白酶原激活剂表达的关键途径。
单一蛋白的检测或者联合几种蛋白加上现有的标记物,如D-二聚体的检测大大提高了急性肺栓塞诊断的准确性。
血栓动脉内膜切除术是治疗慢性肺血栓栓塞症的有效方法。
右心功能不全,左右心室舒张末期的内外径比以及心肌肌钙蛋白I都是判断疾病预后的独立因素。
早期发现右心功能不全对区分高危病人是有利的。
Pang(64)和Yin等人的研究发现急性肺血栓栓塞症(PTE)的患者存在肺血管内皮的损伤,并且凝血和纤溶系统显著失衡。
联合检测血浆D-二聚体、抗凝血酶Ⅲ、蛋白S、蛋白C、血栓调节蛋白、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和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能更好的发现凝血和纤溶系统的失衡。
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有助于平衡PTE患者体内凝血和纤溶系统,并能保护肺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
阻塞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Meta分析显示,连续气道正压通气并不能提高OSAS患者总体的生活质量评分,但能改善患者的体力和精神状态。
研究设计和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表对有效获得患者信息并评估非常重要。
但是,一般的生活质量指标可能无法评估OSAS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变化。
Yue等人通过对中国OSAS患者5-羟色胺转运基因多态性的研究发现,5-羟色胺(与昼夜节律和呼吸节律有关)转运基因与OSAS易感性相关,男性患者尤其突出。
对于OSAS合并高血压患者,反复发生于呼吸暂停终末的运动微觉醒和低氧是影响其昼夜血压水平的重要因素,并可能导致OSAS患者夜间和白天的血压升高。
OSAS患者易患充血性心力衰竭,提示OSAS对心肌收缩力有不利影响。
左右心肌做功指数与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有很强的相关性。
因此,OSAS往往与左右心肌功能受损相伴行。
结论
过去5年中呼吸医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随着呼吸系统疾病分子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大大降低了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现今很多的研究涉及分子免疫、靶向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水平。
尽管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临床实验的结果却很是鼓舞人心。
随着对呼吸疾病发病机制、疾病进展因素和治疗靶向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能更好的评估疾病的风险和预后,并发现新的治疗策略。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在呼吸医学研究领域,我们缺乏尖端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诊断及治疗的循证医学研究。
此外,因为较难获得人体肺脏的组织学标本,上述呼吸医学的进展大都来自动物实验。
我们应注意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并能采用先进的实验技术,如转基因或基因敲除的小鼠来进行研究。
同时,我们需要组织更多的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平行对照,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
总而言之,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减少疾病对人们身心的伤害,使呼吸道和肺免受疾病侵袭。
对此,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呼吸医学研究者任重而道远。
呼吸治疗技术专业要学哪些课程
呼吸治疗技术主要研究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呼吸治疗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面向医院监护病房(ICU)、呼吸科等进行呼吸治疗和危重症监护等。
如:对急性危重病人的通气治疗和氧疗,各种医疗气体的使用与监测,急性危重病人的心肺复苏,ICU急重症病人的肺功能和呼吸监测。
呼吸治疗技术涉及课程有:《生物化学》、《人体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呼吸治疗学》、《重症监护学》、《机械通气》、《呼吸生理与肺功能学》、《呼吸治疗仪器学》、《呼吸系统疾病学》、《健康评估》。
就业方向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机构,如呼吸治疗、危重症监护。
专业培养目标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呼吸治疗等知识,具备呼吸治疗技术监测评估、方案实施、数字化应用和可持续发展等能力,具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及信息素养。
主要专业能力包括:心肺和相关脏器生理与功能的监测及评估,呼吸治疗过程的监测与评估,人工气道管理与自然气道维护方案实施,雾化吸入、气道湿化、气道廓清等呼吸治疗技术方案实施,患者院内外转运或急救中呼吸治疗安全保障工作,呼吸康复的管理、指导与咨询,进行社区、家庭呼吸康复,戒烟指导和呼吸健康宣教工作,参与呼吸治疗相关技术与设备的应用培训和推广,良好的数字化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依法从事职业活动。
实习实训包括:机械通气、气道管理、氧疗、气道廓清、呼吸康复等实训,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呼吸治疗科(组)、ICU、呼吸科、急诊科、辅助医疗(如肺功能检测、睡眠监测与治疗、支气管镜检查、高压氧治疗等)中心,康复医疗中心,社区医疗中心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包括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等。
接续专业包括呼吸治疗技术、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学等。
深呼吸能使身体健康吗
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氧气。
所以,过去人们认为氧对于人体健康十分重要,而视二氧化碳为废气。
为了加速吐故纳新,长期以来不少人提倡做深呼吸运动,以多吸入氧气,多排出二氧化碳。
许多体育爱好者有锻炼之前作深呼吸后,不知为什么,没练几下却突然感到心慌、恶心,甚至出虚汗。
特别是在负荷较大时,更常有发生。
过去总认为这是锻炼者负荷太重或准备活动不充分的结果。
其实,这是做深呼吸造成的。
有人对动物进行了深呼吸试验,结果发现,深吸吸并不能使动物的动脉血液增加氧气,而大量呼出二氧化碳却能导致肺,血液和细胞中二氧化碳含量减少,使神经系统易受刺激,代谢紊乱,直至倒毙。
怎样解释深呼吸对动物的致命性效应?人们认为是二氧化碳大量丢失引起体内气体失衡的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人体对氧和二氧化碳的要求同等重要,血液中必须含有6.5%的二氧化碳和2%的氧才能保证正常的代谢。
而深呼吸却破坏了二氧化碳与投送之间的平衡,使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明显下降,致使血管急剧收缩。
在这种状态下,氧气则会牢固地与血红素结合,导致机体组织难以从红细胞中获得氧气。
这就形成了肺部吸氧过量,而肌体组织缺氧的矛盾局面,从而出现心慌、恶心等现象。
研究者认为,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改变氧气多多益善的传统观念,事实却一再证明,崇氧的前景未必那般美好,倒是低氧、高二氧化碳在一定情况下使人受益匪浅。
在3000米高的山地,空气中氧的含量只有12--15%,这种低氧环境反而对身体健康有利。
山区居民的哮喘、高血压、狭心症、梗塞症患者就少于大气中含氧21%的多氧地区的居民。
前苏联医学家发现了一种用定期呼吸缺氧空气来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
通过让患者反复吸入只有10%的低氧空气,调动人的内在潜力,启动人体应付缺氧的自卫系统的潜在功能,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
据称,这种二氧化碳相对增多的缺氧疗法,在治疗心血管、呼吸及神经系统疾病中有明显疗效。
印度的瑜伽功之所以神奇,奥秘即在于它能减轻呼吸,蓄积二氧化碳。
一些印度医疗部门组织老年哮喘患者进行瑜伽锻炼,一段时间后一些病入膏肓的人竟能屏气10分钟,使沉痼不药而愈。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深呼吸对人体都有害处。
比如处于运动状态的人,因无氧运动使体内积聚的二氧化碳过多,他就会不自主地进行深呼吸运动,直到达到新气态平衡,才能恢复正常呼吸。
运动之所以能健身,可能就在于它能启动机体应付缺氧状态调节机能健身,因而也是最好的缺氧疗法。
为了珍惜二氧化碳,学者们建议人在平静时不必无缘无故进行深呼吸运动,因为只有学会控制呼吸,才能赢得身体健康。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