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导航:
复杂性思维之《规模》
现在社会整体趋势而言是越来越复杂和不连续性,也就对应着不可预测。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暂时的正确给自己笃定的力量呢?《规模》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规模》给我们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从宏观世界中用一种统一框架下去解决一些具象的问题,比如快速城市化、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对癌症、新陈代谢、衰老和死亡的产生原因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数据或者概率, 用数据思维和概率思维来提升我们决策的能力 。
书中的结论虽然是归纳法的形式形成的,但是也有逻辑推导。
比如生物的底层逻辑是代谢率,生命的过程是能量输入、新陈代谢以及熵增的过程,如何才能量化这些系统互相作用?能量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在数量上是通过代谢率体现的,即维持一个生物体存活一秒所需的能量总量。
对我们人类而言,每天需要大约2 000卡路里的食物热量,这仅相当于90瓦特的代谢率,与一只标准的白炽灯灯泡的电功率相当。
但是在能量的转化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可违背的,即每当能量转化为有用的形式时,同时也会产生“无用”的能量作为副产品:一些我们“不期待的后果”总是以难以获取的无序热能或不可用的物质形式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
生物遵循的规律是代谢率规模法则又称作克莱伯定律,该定律适用于所有种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甲壳动物、细菌、植物和细胞。
类似的规模法则适用于所有生物数量和生命史特征,包括增长率、心率、进化速率、基因组长度、线粒体密度、大脑灰质、寿命、树木高度,甚至树叶的数量。
它们都是“幂律”,并且指数都是1/4的整数倍,经典的例子便是代谢率的3/4。
因此,如果一只哺乳动物的体重增长一倍,它的心率便会下降25%。
不管是生物、公司还是城市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度复杂,由大量独立成分组成,都通过不同时空层次上的网络化组织相互联系,不断进化。
网络化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比如社交网络、生态系统等等。
但是生物和公司会死亡,城市为什么几乎不会死亡呢? 这就涉及到规模缩放与复杂性:涌现、自组织和系统韧性。
所谓规模缩放指的是一个系统在规模发生变化时如何做出响应。
如果规模扩大一倍,一座城市或者一家公司会发生什么呢?或者,如果规模缩小一半,一栋建筑物、一架飞机、一国经济、一只动物又将如何呢? 比如城市,所有城市的基本特征,即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率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系统性提高。
这一伴随规模扩大而出现的系统性“附加值”奖励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作“规模收益递增”,而物理学家则会使用更加时髦的术语——“超线性规模缩放”。
具体的数据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而按比例缩放,以近似1.15的超线性指数变化。
也就是说城市的规模缩放指数约为0.85。
我个人认为城市之所以几乎不会灭亡,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熵减的速度大于熵增,城市是创新而非规模经济霸权胜出的代表。
而生物和公司都不是完全开放体。
比如生物,每个生物个体都是一个自适应的复杂系统,典型的复杂系统是由无数个个体成分或因子组成的,它们聚集在一起会呈现出集体特性,这种集体特性通常不会体现在个体的特性中,也无法轻易地从个体的特性中预测。
例如,你远远不是组成你肌体的细胞的集合体那么简单;同样,你的细胞也远远不是组成它们的分子的集合体那么简单。
生物的规模缩放指数约为0.75。
公司的规模缩放指数约为0.8。
那么我们如何以更全面,更整合的方式来思考事物呢?首先复杂系统有如下规则:1、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线性总和,而且整体通常也与其组成部分存在极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部分之间遵从简单规则的互动产生了1+1>2的效果,这种现象叫做涌现行为。
2、许多复杂系统并没有中央控制,他们都是去中心化,自组织、自适应的生态体系。
3、要警惕幼稚地将系统拆分为相互独立的组成部分。
此外,系统一个组成部分的小小不安或许会给其他组成部分带来重大的影响。
4、按规模缩放从小到大的增长通常伴随着从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能保持系统的基本要素或基石不发生变化或被保存下来。
这也就提示我们越是基础的越牢固,我们可以去寻找变化中的不变的要素。
那么,如何思考呢?要用系统的观点来思考,这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其次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度学习U型思考,迭代认知结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断打破假设,建模,重塑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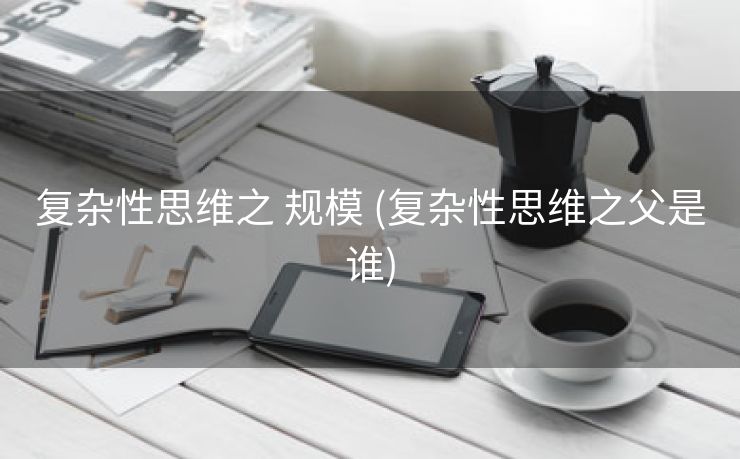
城市地理学笔记
第一章:绪论城市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三级学科,属于人文地理学分支,同时是自然地理学边缘学科,是社会科学中的地理学科,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
第二章:城乡划分与城市地域城市的行政地域通过特定标准或程序设置,确定了市、镇、乡、村的管理边界。
实体地域则是城市本质特征,主要划分城市建成区,以区分城乡。
城市群以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借助现代化交通和信息网络,促进个体城市间联系,形成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
第四次人口普查对城镇人口统计标准:市人口包括设区总人口与不设区市的街道人口,镇人口包括不设区市镇居委会人口与县辖镇居委会人口,总人口则是设区市总人口与不设区市镇非农业人口之和。
第五次人口普查改进了市镇人口划分方法,引入人口密度原则与建成区延伸原则,克服了四次普查的缺陷。
第二章: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不同类型的城市包括中心镇型、交通型与专门化城镇。
第四章:城市化原理城市化分为城市化Ⅰ与城市化Ⅱ,前者涉及地域集中与景观转化,后者是抽象、精神过程。
城市化地域空间过程有正统、假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城市文化扩散等四种情况。
城市兴起与成长的前提包括剩余粮食生产能力与农业劳动力。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型城市化分别指国家投资与农村自筹发展。
城市化指标包括城镇定义、人口定义与城市化水平计算,以及城市化近域推进演化模型。
工业社会时期的城市化特点包括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体系结构变化、世界城市体系形成。
城市经济分为基本与非基本部分,基本部分服务外部,非基本部分服务内部。
影响城市基本或非基本比率的因素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专业化程度与城市新旧。
城市基本与非基本活动对城市发展影响显著,基本活动是城市发展的内部动力。
第七章:城市规模分布首位律定义首位城市为规模巨大、集中全国城市人口的特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占据优势。
首位度是最大城市与第二城市人口比值,反映城市集中程度。
首位分布与城市等级金字塔描述城市规模分布规律,位序-规模法则揭示规模分布模式。
三个阶段我国城市规模分布趋势为:第一阶段增长最快、第二阶段增长最慢、第三阶段有所回升但未达第一阶段水平,呈现马鞍形趋势。
第八章:城市空间分布体系城市联系分为物质移动、交易过程与信息流动三种方式,相互作用条件包括互补性、中介机会与可运输性。
需求圆锥体原理解释市场区形成,廖什景观与克里斯塔勒学说比较分析中心地体系。
第九章:城镇体系城镇体系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不同职能分工、规模等级与联系密切的城镇组成,形成整体性、等级性与动态性的集合体。
第十章:城市土地城市土地概念包括城市建成区、规划区与行政区划范围,西方经济学地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解析。
第十一章:城市内部地域结构均质性是指城市地域在职能分化中保持等质与排斥异质特性,计算公式为均质度D=λ(1-H),均质地域通过特定城市职能形成。
伯吉斯同心环模式与霍伊特扇形模式解释城市土地经济地租机制与城市扩展方向。
城市中心商务区是城市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地价最高,是城市经济发展中枢。
城市开发区是政府或企业规划建设的产业实体进驻区,分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与科学工业区。
城中村定义涉及空间、类型与形成原因,成熟、成长与初生型描述其空间位置、发育程度与与城市用地关系。
第十二章:城市市场空间城市商业布局分为多层次商业中心、带状商业网点与专门化商业区,赫夫商业零售引力公式解析商业布局。
社会区作为研究人口分布与生活方式的地理空间单位,社会区、邻里与社区构成社会地理学研究层次。
居民构想图由路径、界线或边沿、区或区域、枢纽或节点与标志五项要素构成,描绘城市空间感知与认知。
复杂系统研究的发源地——圣塔菲研究所
这些年来,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研究一些复杂系统,研究一些历史经济现象的成果越来越多。
甚至很多成为畅销书了,例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生理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这本书就是从地理环境出发,从而对人类历史演进的原因进行解释,例如财富和权利为何是如此分配,我们在当下是如何经历的,为何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历史为什么不能是另一种样子等。
前段时间还有一本畅销书叫《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作者试图通过物理科学和数学的思想、概念、范式,构建一个可以解释生物体大小、城市规模大小、公司规模大小等高度复杂系统的,具有通用性的“规模法则”。
作者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是享誉全球的复杂系统科学领军人物,并在2006年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他是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曾担任顶尖的复杂系统研究机构——圣塔菲研究所的所长。
圣塔菲研究所是在1984年,由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起,其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瑞·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
他们会同一批从事物理、经济、理论生物、计算机科学的著名研究人员,在美国墨西哥州的圣塔菲伊苏区中一个租来的女修道院中组建了圣塔菲研究所。
圣塔菲的创始人们意识到,科学和社会所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性、令人激动、深远的问题,都处于传统学科的边界之间。
包括,生命的起源,有关生物体、生态系统、流行病或社会的创新、增长、金华和系统韧性的一般性原则,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网络动力学,医学和计算科学中的生物学研究范式,生物学和社会中的信息加工,能量和动力学的相互关系,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等。
圣塔菲研究所致力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跨学科研究,包括物理、计算、生物和社会系统,在国际上被公认为“复杂系统跨学科研究的正式发源地”,发挥着核心作用。
圣塔菲研究所的文化在于创造一个开放的、催化性的环境,把聪明人聚集在一个相互扶持、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并让他们彼此能够自由互动和交流,就将自然而然产生很多思想火花,从而将高度多样化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为实质性、深度的合作做好准备。
这个研究所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设系别或正式小组,而是有着努力推动长期、创造性、跨学科的研究的文化,涵盖了数学、物理、生物医学、社会和经济等各个领域。
二是人员来源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长期教员较少,但是有100名左右的外部研究人员,都在别的机构任职,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圣塔菲研究所待上几周。
三是几乎没有层级结构,同时在这里的人员规模不大,每个人都很容易认识其他人。
四是相互交流非常频繁,可供研讨的公共区域非常多,可以边吃午餐,边即席研讨,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古生物学者、量子计算专家、在金融市场工作的物理学家等可以每天互动交流,相互交谈,共同思考。
圣塔菲研究所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由前面提到的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和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发起,旨在从复杂系统的视角去解决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例如非线性系统、统计物理学和混沌理论如何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洞见,在1989年就创建了早期研究小组,尽管现在这种学科组合已经不再罕见,但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合作,被称为“科学史上最为奇怪的组合之一”。
评论(0)